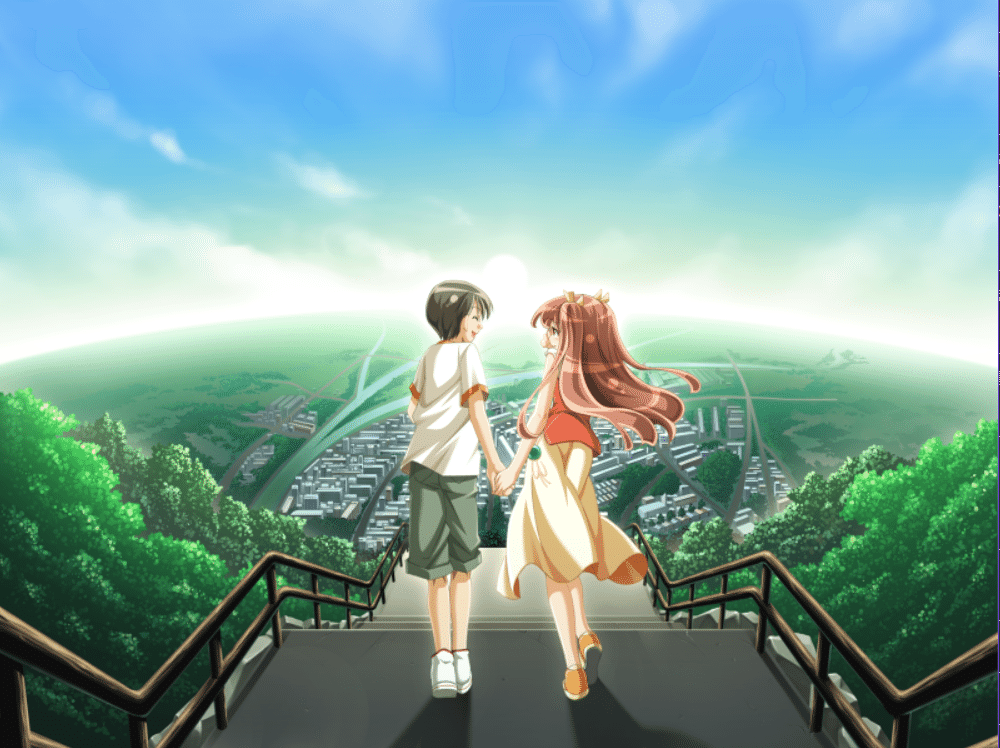荒誕、幸福與拯救 — 瀨戶口廉也《Carnival》感想/考察
《Carnival》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在批評空間裡《Carnival》被標記為サイコ陵辱ノベル。サイコ (psycho)這個字緣於心理病態 (psychopathy)﹐也是對男主角木村學的形容。形容一個人サイ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也就是相對其他人來說這人更為心理病態。遊戲裡的木村學完全符合犯罪型心理病態 (criminal psychopathy) 的特徵﹐因心理病態而犯下了殺人、凌辱的行為。在壓抑的情況下成長的木村學衍生出一個更具攻擊性的人格ー木村武。這種解離性身份疾患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很大程度是緣於童年時受到創傷,透過構造另一個人格減低自己受的傷害。遊戲裡也寫到木村武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殺掉欺凌他的學長﹐也就是說木村武的人格是負責應對欺凌的情況。這個更具攻擊性的人格為了改變這個情況而決定殺掉了欺凌他的學長﹐在逃走後和青梅竹馬的理紗進行逃(復)難(仇)的旅程。

《罪與罰》﹐尼采的道德觀
這遊戲的開始令我想起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在《罪與罰》裡面﹐男主角拉斯柯尼科夫是一個窮苦的大學生。他居所附近住了一個掌管當鋪的老太婆﹐她十分吝嗇﹐只願意付很少錢來進行收購。拉斯柯尼科夫有這樣的理論: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虱子﹐另一種是統治者。統治者是凌駕於法律﹐不受道德的約束。他殺了老太婆﹐還殺了目擊事件的老太婆的妹妹﹐搶走了金銀財寶。對於他的行為﹐拉斯柯尼科夫並不覺得自己有罪。
木村武和拉斯柯尼科夫非常相似。當然他沒有像拉斯柯尼科夫般瘋狂﹐他還有理紗都對自己的行為有罪惡感﹐也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確。關鍵點是在於有別於傳統基督教的善惡道德﹐他們的行為更像尼采的道德哲學ー為生命賦予意義。木村武殺死欺凌他的學長的主要原因是反抗﹐改變現狀﹐其本質就是透過改變來尋找木村武人格自身的意義。尼孚的善惡彼岸道德提出的新道德是一個生命哲學﹐將生命置於道德之上。相比起理性﹐本能是更真實的事物。在瀨戶口的筆下﹐木村武的殺人是對於生命力受到威脅的本能反抗﹐擁有自主道德的木村武(學)﹐還能被稱為不道德或者是惡人嗎?
追着紅蘿蔔跑的馬﹐《薛西弗斯之神話》
《Carnival》裡有一個關於幸福的比喻ー追着紅蘿蔔跑的馬。在馬的頭上裝上釣竿﹐掛上一個紅蘿蔔﹐馬就會一直追着紅蘿蔔往前跑。理所當然﹐馬跑上一輩子都追不上紅蘿蔔。小時候的理紗﹐認為幸福就像那紅蘿蔔一樣﹐怎樣都追尋不了。這個比喻和卡繆 (Albert Camus) 的《薛西弗斯之神話》十分相似。在薛西弗斯之神話》裡﹐薛西弗斯因得罪宙斯被懲罰。在他逃走享樂後再次被抓﹐眾神決定懲罰他永遠都要將石頭推上山上﹐但石頭到達山頂後會滾回山底﹐薛西弗斯就要再次將它往上推﹐永續地重覆這動作。卡繆認為薛西弗斯知道推石頭是無意義的事情﹐但他仍然去做以作為對眾神的反抗﹐因此我們應該認為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將《薛西弗斯之神話》套用到追着紅蘿蔔跑的馬的比喻上﹐就會發現我們應該認為追着紅蘿蔔跑的馬是快樂的﹐即使他知道永遠都追不上那紅蘿蔔。當理紗再次和學談到這比喻時﹐她認為即使她永遠都追不上那紅蘿蔔﹐但卻依然不想後悔地繼續奔跑下去。

能拯救人的是神、還是人?論卡繆的荒謬
在《罪與罰》裡面﹐拉斯柯尼科夫遇到信仰虔誠的索妮雅並受到感悟﹐最後皈依東正教懺悔。《Carnival》在此則和《罪與罰》完全相反。在《Carnival》裡瀨戶口完全展示了反基督教的一面 (在キラキラ和swan song也可見)。理紗在閱讀了《聖經》以後﹐她反而是幫助學去復仇﹐反抗這個荒謬的世界。
卡繆的荒謬 (absurdism) 有兩個基本前設:
1. 人有內在的慾望去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 (ultimate meaning)。套用到《Carnival》裡面﹐學和理紗一直在尋找的終極意義就是「幸福」。
2. 世界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就是全部可以說的 。在《Carnival》這反映自學和理紗受到的家庭暴力和學在學校被欺凌。
荒謬就是來自於這兩個前提的對立。世界的不合理妨礙了人去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卡繆指出我們不能靠自殺或者信仰的飛躍 (leap of faith) 逃離這個荒謬的情況。前者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人的命就只有一條﹐死了就無法繼續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而信仰的飛躍則會令到人無視理性﹐依靠信仰去相信事實﹐從而失去尋找終極意義的慾望。要逃離荒謬﹐卡繆指出只有在持續意識到荒謬的存在下反抗這個荒謬。
這能解釋理紗的行動。她並不是盲目去幫助學。她是在和神父接觸、閱讀聖經後﹐否定了信者得救的信念﹐靠自己的行動去拯救學。這也是瀨戶口筆下最美麗的一面:在這荒謬的世界裡﹐能拯救人的並不是神而是人。
所以﹐《Carnival》是一個怎樣的作品?
這是一個非常意識流的遊戲。比起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更重要的是這些事象徵些什麼。家庭暴力、欺凌象徵荒謬﹐武的復仇和理紗的協助是對世界的荒謬的反抗。記得曾經在網上看過瀨戶口的訪談說他其實不喜歡寫galgame﹐在《Carnival》亦可見其原因。雖然在劇情混入了凌辱、殺人的情節﹐但這些都只是復仇的象徵﹐甚至連H scene都是由他人代筆。瀨戶口的狂氣並不依賴對這些情景的描述來表達。相比起劇情﹐更狂氣的大概是瀨戶口背後的信念 (可以參考瀨戶口的小說《電氣馬戲團》和《Psyche》﹐那是壞掉的人才寫得出來的作品)。
《Carnival》遊戲裡的結局中﹐學和理紗完成了對雙方的救贖。但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結。在後傳小說裡﹐在逃亡旅程看到幻覺的學走向了自殺的結局。很荒謬卻又很真實的結局。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瀨戶口不喜歡寫galgame:在感動的結尾後再放一個反高潮的結局是絕對會被寄刀片 (看看新島夕的爭議就知道了) 。但這反高潮的結局卻令《Carnival》昇華至另一個層次。學無法像理紗般原諒自己﹐他殺了人、犯了罪。他沒有被懲罰﹐但這個罪惡感會一直存在於他﹐還有理紗的心中。這個罪惡感的代價就是學的精神崩潰﹐以及見到精神崩潰的學而受傷的理紗﹐到最後學為了保護理紗而自殺。
《Carnival》就是一個這樣充滿缺憾美的故事。雖然學和理紗都得到了幸福﹐但最後能得到拯救的只有理紗。為了理紗能得到拯救而犧牲的學。瀨戶口筆下就是一個這樣荒謬的世界﹐為了反抗這荒謬的世界而拼盡全力﹐屬於學、武﹐和理紗的故事。
This world in itself is not reasonable, that is all that can be said.
但即使這樣﹐我仍然想愛這個世界。